我的先生陈家坪,他是一个天性非常非常温和的人,颇有些宠辱不惊的气度。他同时也非常克己,自尊且自律。他待人接物很宽容,甚至有些木讷,受了欺负都感觉不到。这往往令我非常恼火,所以在无意之间,就扮演起了一个保护者的角色。这么多年,我自己对朋友同事都很“慈祥”,但和他在一起就变成了母老虎,和他的不诚信的朋友打过官司,和仗势欺人的保安打过架……我自己遇到能一笑了之的事情,发生在他身上,就变成了过度保护。
我的这种过度保护,一方面当然是出于爱,更多还是对他品格的折服。首先是陈家坪对文学的追求,一个从农村走出来,没有受到过非常系统的大学教育的人,在诗歌创作和文学艺术评论方面取得过一点点成绩,和他多年刻苦的学习和阅读是分不开的。另一方面,我认识他的时候,他正在拍“教育公平”的题材。作为一个诗人,他始终试图从生活中寻找诗性,从现实中寻找表达方法。他拍当时代表抗争精神的人大代表,拍那些具备初级公民意识的,为自己也为他人子女争取受教育权利的家长和孩子,希望用丰富和多元的视角,补充诗歌对现实的无力感。但是他根本不会拍,事无巨细,风雨无阻,拍下了几乎每一个他看到的现场。这些场景、人物、事件,很多在剪辑过程中被认为是不具有意义的,但是他都记录了,他不舍得落下任何一个瞬间。
这样的记录方式笨拙而耗费精力,而且没有酬劳,但他乐此不疲。那时,他过得很苦,出租屋非常简陋,除了电脑和一个别人淘汰的机械式大电饭锅之外一无长物。馊了的稀饭还在一顿接一顿地吃,生活到了极简的程度,省下的时间和精力,就用来读书和拍摄。拍一次活动需要一整天,回看还需要一整天,把它们有逻辑地剪辑起来,可能就需要更久,一周、一个月、一年,都有可能。我们结婚以后的这些年,除了穿衣吃饭有了保证之外,他始终保持着简单和清苦的个人习惯。为了形成一部说得过去的作品,他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记录—剪辑—记录—剪辑,周而复始。有时候,他还会把我拉进去做场记,我根本没有这个耐心,但是为了他的创作,也不得不陪他夜以继日,然后再眼看着他的“作品”被前辈或者同道否定,一切重头再来……
但是他还是坚持。我想,能坚持的人不多了,为了理想坚持,不管不顾的人就更少。虽然我很难免不恨恨不平——生活和未来的压力都在我这里,凭什么你就可以追求你的精神世界?但是我还是支持他,就因为,他是我的爱人,他是与众不同的,世间少有的,至真至纯的人。我常常为一首歌感动:“那一天,我丢掉了你,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……”我曾经根本没有过玩具,更曾经错失了我曾经追求过的一切,所以我,不能眼看着陈家坪失去他的追求,他的执著,成为一个特别特别无所适从的人。对于陈家坪来说,用笨拙的方式记录现实,直到现实成为历史,就是他的唯一追求。所以,我不戳穿他天资的不够、他的技巧与方法的不足,成不了纪录片就成不了吧,至少那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。
但是我所没有想到的,是他为他的记录而失去了自由,因为记录了一段历史而被冠以“涉嫌煽动颠覆”的罪名而失去自由,并且突破了100天,至今仍然没有特别令人安心的消息。记录生活和历史有什么罪过呢?尽管他记录的是反对的历史,是抗争的历史,但是这个历史是真实存在的,是可以“惩前毖后”的,也是当权者能够、可以,甚至必须用来自我革新的现实镜子。我不认为他有“煽动”的意图,首先一个政权有其自身的坚固性;第二,历史曾经证明,“兼听则明”。死于“独家报刊”的袁世凯,垂危之际终于懂得了这个道理,但是为时已晚。而我们的政府,拥有敢与世界抗衡的强大智囊,他们都应该懂得,多渠道信息的重要性。一个群体的悲惨世界如何能被视而不见呢?一个异议者的精神世界怎么能够被忽略?如果我们都去帮闲般地高唱“恭喜”,政权真的就能够万世永固吗?我认为这个道理,妇孺皆知。
但是他还是被抓起来了,以山巅的名义,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至今,已逾105天。他们在查抄了所有的电子设备和素材之后,给他带上手铐和黑头套带走了,而且至今不能够给我一个基于司法的合理说辞。
而这一次,我保护不了他了。我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体,而是一个公权力机关,这个机关拒绝与我委托的律师通话,拒绝告知我所谓案件的进展。我不但无法了解我先生目前的身体状况、精神状况、他的处境,更无法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重获自由。我所有的语言、所有的愤怒都没有用武之地,就像人贩子死死扭住孩子细嫩的胳膊时,在恐惧和心疼中无奈放手的母亲。
但是,我最终相信,陈家坪并不是一个有意寻求保护的弱者,在他的精神世界里,有一些事情是终究不能让步的,有一些原则是他始终恪守的。经过狂流的涤荡,陈家坪不事权贵、倨傲独得的品格始终会一如既往。我同时也相信,每一个涉案人员、办案人员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当时代的尘埃落定之时,当我们回首人生之路,能不能禁得起“问心无愧”这样的追问?如果不能,我们就不能谈到爱祖国、爱人民。
所以陈家坪,我不但相信你很快就能重获自由,并且相信你能够得到你所追求的,创作和表达的自由。
我和全部的家人,和全部关照、关爱你的人,一起等你。
李泽慧
二O二O年六月十五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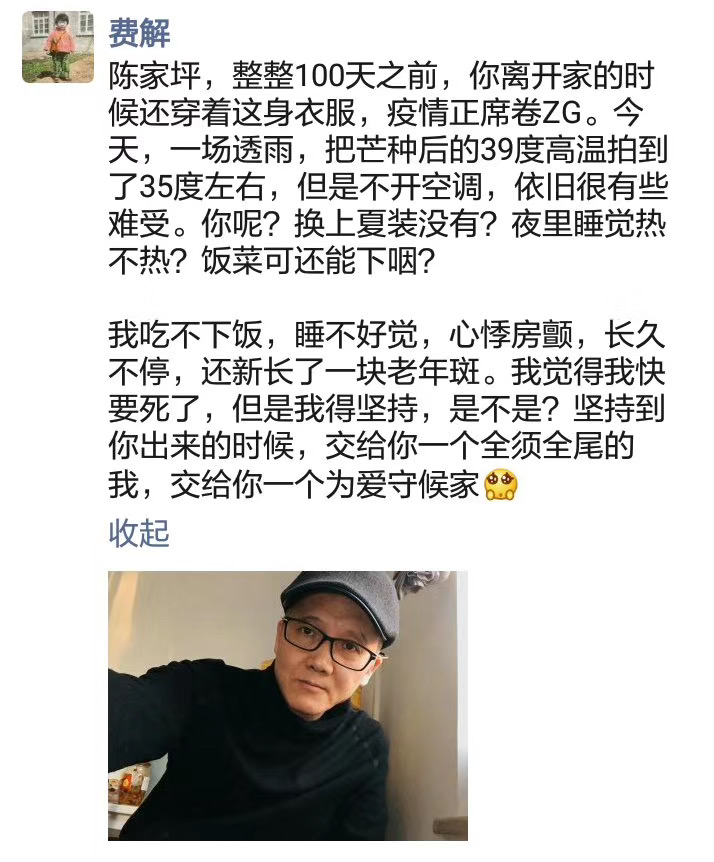
公民来稿
